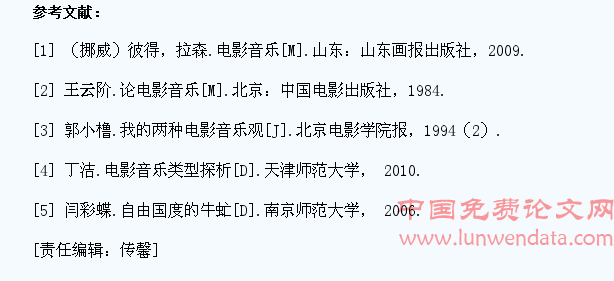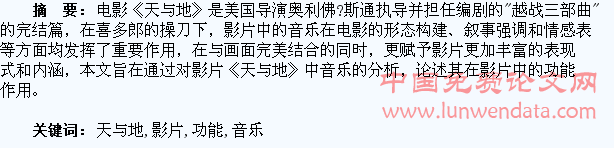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6-0101-02
电影《天与地》是由美国导演奥利佛?斯通执导并担任编剧的“越战三部曲”的完结篇,不同于前两部电影《野战排》和《生于7月4日》的男士视角,《天与地》是从东方女人的角度来考察战争,呈现出一种极具温顺神秘的东方色彩,给人以一种委婉而又壮美的感受。同时,影片中的配乐在电影的形态构建、叙事强调和情感表达等方面均发挥了要紧用途,使得整部影片彷佛是一曲历史与现实的合奏,带给人灵魂深处的震颤。
1、形式功能――塑造电影形态,构建叙事结构
彼得拉森在《电影音乐》艺术中觉得电影音乐的形式功能重在电影音乐在构建电影形态和结构上有哪些用途,音乐能使电影连贯起来,赋予电影以整体感,在《天与地》当中,主题音乐《heaven and earth》贯穿于整部电影,并在不一样的阶段反复出现,依据剧情进步的需要变奏,将不一样的片段场景统一于同一个主题下,通过讲解战争所导致的人性悲剧传达对战争的控诉和对和平的追寻。同时,喜多郎还使用乐旨来构建电影音乐的连贯性,在《天与地》中乐旨即为战争与人性,它贯穿整部电影配乐,将不一样的场景音乐片段包含越南家乡、美越战争、黎丽的爱情、西贡的生活、回归故土等连接起来,凝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影片配乐使用运用管弦乐的磅礴和古筝、笛子、二胡之间的柔美来形成战争和生命两个形象上的对比,既架构主题之间的统一性,又加大各音乐片段之间的联系和辨识度,使受众形成视听感知上的一致性。
除去构建电影形态,音乐还可以帮助构建影片的整体叙事结构,电影音乐可以帮助受众正确对影片中的信息进行归类。譬如每当黎丽爱情主题曲响起时,受众自然会预感到黎丽马上与当下的男主人公发生感情纠葛,而当悠远苍凉的二胡笛声旋律响起时,受众则会联想到黎丽的故乡越南。同时音乐的变化标志着不同叙事段落的衔接和转换,譬如在五邦参军,黎丽的爸爸和她在田野上交谈后,影片的音乐开始从辽阔广远的柔和风格转为携带激昂鼓点的进行曲,随着而来的剧情则是残酷战争的开始。音乐之间连续性又暗示了两个段落之间的联系,使受众的情绪得以连贯,不会产生断裂和突兀的感觉。
2、叙事功能――强调叙事元素,调节叙事步伐,塑造人物形象
电影音乐叙事功能即电影音乐在叙述故事时所起到有哪些用途。这也是《天与地》中音乐所起到的非常重要的功能。电影中的配乐一直会带有特定的地域人文色彩和不一样的年代特征。譬如最典型的就是《天与地》中在表现黎莉的家乡越南时,所使用的是温顺的管弦乐配以二胡、古筝、笛子和越南民族乐器,塑造出的是一种辽远凄凉的环境。而当黎丽来到美国生活,场景音乐则变成了步伐明快的乡村摇滚,充满了时髦和摩登的气息,黎丽在超市一脸满足的看着产品时所配的欢快的《蓝色多瑙河》交响曲,映衬着美国富足的物资和优越的生活环境,这同时也与贫苦的越南生活形成鲜明的反差,形成“天”与“地”的对比。除此之外,电影音乐可以用于强调和预期电影当中的单个事件。有时,电影仅凭着一小段旋律的变化就能引发大家做出相应的反应和猜测,譬如斯蒂文在自杀前打电话给黎丽,这个时候音乐旋律变得低沉恐怖而诡异,受众立刻就能预感到某种不祥的讯息。因此音乐独特的音色、音调和旋律可以刺激受众的听觉神经,调动受众的注意力,令他们产生心理上的期待,从而积极调动他们的情绪感受。
除此之外,在电影叙事中,音乐还能起到调节影片步伐和塑造人物形象的功能,在对电影的叙事步伐进行调控和构建上,影片中常常出现大段场景描绘越南自然风貌的镜头,若是单纯的画面呈现,纵使画面再震惊,受众也非常快会感到枯燥,但配上音乐则不同,波澜壮阔的旋律以其自己的魔力使受众在视听共享中忽视了影像的单一和缓慢的步伐,从而调节了受众的心理时间,“加快”了影片叙事的进程。而在黎丽和斯蒂文家里遇袭再到西贡团圆这一段里,电影音乐有效地调节了影片叙事的张弛程度,在家里遇袭时,影片并没使用快步伐的配乐来激起更为紧张的氛围,而是运用磅礴低沉的管弦乐来调节画面中的激烈冲突,呈现出一种情绪上的压抑,这种压抑感在黎丽携带孩子边逃难边找老公的过程中持续加深,一直到受众也开始绝望的时候,音乐的旋律忽然开始渐渐上扬,伴随一声“Daddy”镜头随后转到从远处走来的斯蒂文身上――原来他还活着。这时音乐旋律达到高潮,前面的失望,痛苦,在重逢这一刻中的得到完全释放,迸发出一种巨大的幸福和喜悦感。虽然影片中的画面和演员表演所带来的信息量与信息质已是这段情节形成基本叙事步伐的基础,但若仅凭着画面和演员的动作,这种内在汹涌的能量依旧很难得到释放,但配上电影音乐就能表现叙事步伐内部潜藏的所有能量。
同时,《天与地》中的配乐在影片中亦起到了塑造人物形象的“代理功能”,作曲者喜多郎借用联觉将声音的特点与人物的外形、性格、心理等特点联系起来,从而用音乐来描绘人物。正如前面提到的,影片主题曲《heaven and earth》不止是对战争的控诉和人性的关怀,同样也是黎丽个人命和形象的写照,而她的命亦是越南的命。二胡、笛子、古筝所奏出的细腻而又伤感的旋律刻画出黎丽的女人气息与苦难阴影所带来的忧郁特质,而磅礴深沉的管弦乐则体现出黎丽柔弱外表下坚韧不拔的性格特点,用她的宽容和坚强与虽然减弱但从未消失的信仰来承受所有苦难。这种信仰来在于爸爸从小对她的教诲。而在影片中,爸爸形象出现时总是会随着着清净祥和旋律音乐,黎丽在结尾处第三梦到了她的爸爸,此时的音乐是随着着钟声的女孩哼唱,带有一种佛教特有些安详色彩,烘托出爸爸的慈爱和如水一般澄澈宁静的品格,而随后的画面则是黎丽在祥和的乐声中给全村死难者上香,这也是爸爸从小教给她的为人向善的道德准则的体现,爸爸对她的影响早已渗入骨髓,从来不会磨灭。因此电影音乐可以深入挖掘演员内心的情感,表达“演员所不可以表现、讲述的东西[1]”。 3、情感功能――塑造环境,传递情感
彼得?拉森觉得,音乐能“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叙事中,或者在单个部分内部,塑造出‘情感’和‘氛围’……有时,音乐可以积极地塑造叙事的氛围,更准确地说,向观众指示出某一特定场景应该如何理解和体验。[2]”在影片《天与地》当中,电影配乐具备高度的概括性,并能言说画面言外之意,因而在渲染氛围,揭示人物内心世界,调动受众情感上发挥了极其要紧有哪些用途。
整体上而言,《天与地》的电影配乐是“交响乐散文诗”曲调舒缓而宽广,散置的长气息乐句铺满了整部影片,渲染出整部影片辽阔博大的环境。整部影片的音乐并不是是亦步亦趋的刻板的音画同步,而是以俯视的姿态,游离的方法审视画面,正是由于和画面保留着肯定的审美距离,使得影片的音乐具备高度的概括性和包容性,赋予影片史诗般的情怀。而同时在剧情范围内的相对不确定性又可以提供给观众愈加丰富的情感,譬如在黎丽偷偷回到家乡看望爸爸妈妈时,她走在家乡的田埂上,一路上看着被战争摧残的故土和贫苦的村民,背负上叛徒的骂名过得异常辛苦的爸爸妈妈,随着音乐《walk to viliage》响起,低沉缓慢的管弦乐和浑厚的圆号,凄凉的箫声交织在一块,传递出主人公内心很难名状的复杂情绪,对满目疮痍的故乡的心痛,对同胞的同情,对自己悲惨命的感慨,对心中信仰的怀疑和失望,对战争的憎恶…….这种复杂的心理活动如若仅靠言语和动作势必会看上去单薄无力,但音乐所拥有的多义性和高度概括性使之可以唤起受众丰富的联想,赋予受众以高于情感认可体验的理解能力,此时的电影音乐“不止是影片整体情绪基调的显示器,它更作为一种独立的理性意念而积极地参与到画面的造型中去。[3]”
导演自己对于影片的多义性情感亦通过影片配乐得以抒发,影片中富诗意的交响乐与东方法的极致美感感伤与越南战场的残酷形成反照,战争场面并不是音乐的着眼点,导演想要借音乐讲解的是战争背后对人类命的考虑和人性的追寻,在战争面前,人的命,国家的命好似坦克底下的一芥野草,在一种文明的过程中颠沛流离,而喜多朗的音乐则融合了对历史、自然、文化的考虑和感悟,将斯通这个越战老兵内心对于越战的愤怒和批判以一种“无言”的方法表达出来,同时也让斯通内心强烈的负罪和愧疚感得到释放。
4、结 语
从以上剖析中可以看出在影片《天与地》音乐有着要紧的地位,整部影片的音乐在喜多郎的操刀制作之下具备鲜明的个性,西洋管弦乐、越南民乐,与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乐器的综合运用对电影的情调和环境予以了恰到好处的渲染。真的 “在内容、形象、形式、风格上与影片相一致、融为一体”[4]。同时,影片中的音乐在构建影片整体结构形态、参与叙事进程、强调叙事元素、塑造人物形象、表达情感、渲染环境氛围、升华主题上都起到了要紧有哪些用途。这一方面取决于作曲家深厚的音乐功底,其次也是导演个人追求写意艺术形式的表现,作为一个浪漫主义的导演,他习惯于将我们的个性和考虑融入电影的创作,因此,对于音乐的主观性运用亦使他对视听语言的处置超越电影了文本,为《天与地》这曲战争中的女人悲歌增添了更多独立美学上的色彩。